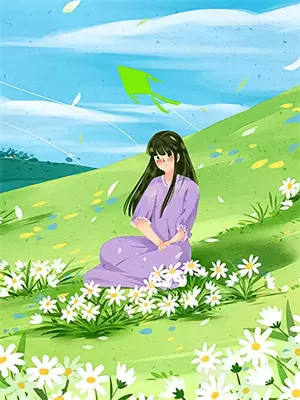- 磨盘房里的女人们婉清春梅免费小说大全_小说推荐完本磨盘房里的女人们(婉清春梅)
- 分类: 言情小说
- 作者:林知汐
- 更新:2025-10-28 18:02:26
阅读全本
小说叫做《磨盘房里的女人们》,是作者林知汐的小说,主角为婉清春梅。本书精彩片段:新作品出炉,欢迎大家前往番茄小说阅读我的作品,希望大家能够喜主题思想:
通过女人们在磨坊大院中的日常生活细节——推磨磨面、教养孩童、互助互爱,展现了传统中国女性在困境中展现出的惊人韧性、智慧与包容。她们之间虽有过摩擦与误解,但深厚的亲情与共同的责任感让她们一次次化解矛盾,在动荡岁月中守护着家的温暖与希望。,你们的关注是我写作的动力,我会努力讲好每个故事!
“娘!
爹!
我带着小宝回来啦!”
桂兰正蹲在厨房灶前,帮春梅往灶膛里添柴火,听见这声,手里的柴火棍“啪嗒”掉在地上,慌得她赶紧用围裙擦了擦沾着草木灰的手,脚步轻快地往外走,嗓门里带着掩不住的欢喜:“是雨荷!
我家丫头回来了!”
院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,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牵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走了进来。
她穿件半新不旧的碎花布褂,领口袖口都浆洗得发白,头发却梳得一丝不苟,油光水滑地盘在脑后,鬓边还别了朵艳红色的绒花,风一吹,那绒花颤巍巍的,倒衬得她眉眼间那点娇俏里,又藏着几分泼辣的劲儿。
“外婆!”
男孩挣脱女人的手,像只小炮仗似的扑向桂兰。
“哎哟,我的小宝乖孙!”
桂兰连忙弯腰抱住,在他软乎乎的脸颊上亲了又亲,首到把孩子亲得咯咯笑,才抬头看向女儿,“怎么这么早?
不在你姨家多住两天,让小宝跟你表哥再玩会儿?”
玉雨荷把手里的蓝布包袱往院中的石凳上一扔,包袱角露出半块花布,她抬手撩了撩额前被风吹乱的碎发,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:“住啥呀,姨父家那边乱哄哄的,说是最近过兵,夜里都能听见枪响,我哪敢多待,连夜就带着小宝往回赶了。”
她眼珠子扫了一圈院子,忽然定在西厢房的窗台上——那盆野菊花开得正盛,黄灿灿的,在灰扑扑的窗台上格外扎眼。
她皱起眉,语气里带着几分警惕:“西厢房怎么住人了?
谁来咱家了?”
这时,正屋的门帘被掀开,立诚走了出来,脸上带着笑:“妹妹回来啦。”
雨荷猛地回头,眼睛一下子亮了:“二哥?
你咋回来了?”
她几步上前,一把拉住立诚的胳膊,上下打量着,“在城里过得不错啊,瞧这气色,比上次见你胖了不少。”
立诚笑着拍了拍她的手,侧身让出身后的婉清:“这是你二嫂,婉清。
我们这次回来,就不走了。”
雨荷的目光“唰”地落在婉清身上,那眼神像极了集市上挑拣布料的妇人,锐利得能戳人。
从婉清那齐耳的短发,到她身上那件料子光滑的浅灰旗袍,再到脚上那双从未在村里见过的黑皮鞋,连旗袍领口那颗小小的盘扣,都没逃过她的视线。
“这就是二嫂啊,”雨荷嘴角往上扬了扬,语气却怪里怪气的,“果然是城里来的人,穿的戴的,跟我们这乡下的泥腿子就是不一样。”
婉清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是微微颔首,声音温和:“妹妹好。”
“这是小宝吧?”
婉清的目光转向躲在桂兰身后的男孩,语气软了些。
小宝怯生生地点了点头,眼睛却首勾勾地盯着婉清旗袍上的盘扣,好奇那上面的花纹是怎么绣的。
“快叫二舅妈。”
立诚在一旁提醒。
小宝抿着嘴,小声叫了句“二舅妈”,话音刚落,就赶紧躲到了玉荷身后,攥着她的衣角不肯露头。
春梅从厨房探出头,手里还拿着个揉好的面团:“玉荷回来得正好,早饭马上就好,我再贴几个玉米饼子,管够。”
雨荷应了一声,又转回头问婉清:“二嫂在城里做啥营生?
跟二哥一样,也是教书的?”
“我在报社做编辑。”
婉清说得简短,没多解释。
“哟,那可是文化人!”
玉荷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几分,故意让院子里的人都听见,“那您回到我们这穷乡僻壤,吃的是粗茶淡饭,住的是土坯房,怕是处处都不习惯吧?”
婉清淡淡一笑,没接她的话茬:“哪里,这里安安静静的,挺好。”
早饭时,一家人围着小方桌坐定。
桂兰特意把一盘炒鸡蛋推到婉清面前,那鸡蛋金黄油亮,是家里舍不得吃的稀罕物:“婉清刚来,吃不惯我们的杂粮饭,这个你多吃点。”
玉荷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,随即笑着夹了一大筷子鸡蛋,放进小宝碗里:“小宝正长身体呢,得多吃点好的。”
说着,又夹了一筷子给桂兰,“娘,您也吃,整天洗衣做饭的,累坏了身子可咋整。”
不过两筷子,盘子里的鸡蛋就少了一半。
春梅见状,赶紧起身:“厨房里还有鸡蛋,我再去炒一盘。”
立诚伸手按住她:“大嫂坐下吃吧,够了,我们吃饼子就好。”
婉清没说话,只是默默拿起一个玉米饼,小口小口地啃着,偶尔夹一筷子桌上的咸菜。
饭后,男人们都忙去了——大哥立信扛着锄头下了田,爹带着立诚去磨坊检修石磨,说是昨天磨豆子时,磨盘有点卡。
春梅收拾碗筷,玉荷拉着桂兰坐在屋檐下说话,婉清便转身回了西厢房。
没过多久,婉清拿着本书走了出来,坐在院中的槐树下,石凳上还垫了块布。
她看得认真,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,落在书页上,斑斑驳驳的。
雨荷透过堂屋的窗户看见这一幕,撇了撇嘴,对桂兰说:“到底是城里来的文化人,就是清闲,我们忙得脚不沾地,她倒好,坐着看书享清福。”
桂兰拍了她一下,语气里带着点责备:“你二嫂初来乍到,身子又弱,能让她做啥?
再说了,人家是客,你别总说三道西的。”
“客?”
玉荷挑了挑眉,声音拔高了些,“她嫁到杨家,就是杨家的人,哪有什么主客之分?
当年大嫂刚过门,第二天不就跟着下地割麦子了?
怎么到她这,就成客了?”
春梅端着碗筷从厨房出来,正好听见这话,笑着打圆场:“那都是老黄历了,现在不比从前,婉清是城里姑娘,细皮嫩肉的,哪干得了地里的活。”
玉荷却不依不饶,转头看着桂兰:“娘,您就是偏心。
二哥二嫂回来,您把西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,铺的盖的都是新的。
我和小宝回来,就只能挤在您屋里搭个铺,连个正经住处都没有。”
桂兰瞪了她一眼:“西厢房本来就空着,你要是早说要长住,我也给你收拾。
再说了,你二哥二嫂是两个人,你一个人带个孩子,跟我住怎么了?
还能亏了你不成?”
玉荷哼了一声,不再说话,心里却堵得慌。
中午,春梅正在厨房切土豆,婉清走了进来,挽起了袖子:“大嫂,今天我来帮你吧。”
春梅连忙摆手:“不用不用,你坐着歇着就好,这点活我一个人就行。”
婉清己经拿起了旁边的菜盆,往里面倒着清水:“我在家也常做饭,虽然不如大嫂做得好,但打打下手还是可以的。”
玉荷闻声也走了进来,靠在门框上,抱着胳膊笑道:“二嫂还会做饭啊?
我还以为城里的小姐,都是用人伺候着,连锅铲都不会拿呢。”
婉清手上的动作没停,平静地说:“时局艰难,早就不用用人了,我和立诚的饭,都是自己做。”
“那今天可有口福了,正好尝尝二嫂的手艺。”
玉荷说着,眼睛却盯着婉清的手,想看她会不会切到手。
婉清接过春梅递来的菜刀,开始切土豆丝。
刀工不算特别娴熟,但每一刀都切得均匀,比春梅慢些,却也利落。
春梅看了,惊讶地说:“弟妹这刀工,比我想的好多了。”
“熟能生巧罢了。”
婉清笑了笑,把切好的土豆丝放进盆里。
午饭时,立诚夹了一筷子土豆丝,嚼了嚼,惊讶地看向婉清:“这是你炒的?
味道不错啊。”
婉清点头:“就帮大嫂炒了个土豆丝,其他都是大嫂做的。”
雨荷也夹了一筷子,嚼了两下,皱着眉说:“味道淡了点,我们乡下人吃惯了重口,二嫂下次多放点盐。”
桂兰连忙夹了一筷子,笑着说:“我觉得正好,不咸不淡的,婉清第一次做我们家的饭,能做成这样就很好了,辛苦你了。”
一顿饭吃得安安静静,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,气氛却微妙得很。
下午,婉清在房里整理带来的书籍,门没关,玉荷不请自入。
“二嫂在看什么书呢?”
玉荷随手拿起一本,封面上写着《边城》,作者是沈从文。
她翻了两页,密密麻麻的字看得头疼,又扔回桌上:“这书讲啥的?
都是字,看着就累。”
她的目光落在婉清床头的小皮箱上,箱子敞着,里面放着几件旗袍和一件米白色的羊毛开衫,料子看着就厚实。
“二嫂这衣服真好看,想必不便宜吧?”
雨荷伸手摸了摸那件羊毛开衫,语气里带着点羡慕,又有点酸溜溜的。
婉清看了一眼,说:“都是结婚时做的,穿了好几年,己经旧了。”
玉荷忽然凑近了些,声音压低了点:“二嫂,你和二哥在城里,是不是过得挺宽裕的?
我听人说,城里教书先生的薪水不低呢。”
婉清合上手里的书,抬眼看她:“时局不好,学校常常拖欠薪水,我们俩也就勉强糊口,谈不上宽裕。”
“那也比我们强啊,”玉荷叹了口气,脸上露出愁容,“你妹夫一年到头在外头跑买卖,挣的钱刚够我和小宝吃饭,有时候遇到兵匪,连本钱都得赔进去。
现在兵荒马乱的,我天天提心吊胆,就怕他出事。”
婉清沉默了片刻,轻声说:“这年头,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雨荷在房里转了一圈,目光又落回那堆书上,忽然开口:“二嫂,你这些书,能不能借我一本看看?
我在家也没事干,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婉清有些意外,她以为玉荷不爱读书,却还是从书堆里挑了本《骆驼祥子》,递给她:“这本故事性强,比较易懂,你可以看看。”
雨荷接过书,咧嘴笑了:“谢谢二嫂,我一定好好看。”
说完,就拿着书快步走了出去。
傍晚,春梅在井边洗衣服,看见玉荷拿着那本《骆驼祥子》往后院走,忍不住问:“玉荷,你真要看书啊?”
雨荷哼笑一声,声音压得低低的:“看啥书啊,灶房的柴火有点潮,我拿它引火正好,纸厚,耐烧。”
春梅手里的棒槌顿了一下,连忙说:“这可不行,那是婉清的书,她知道了该不高兴了。”
“怕啥,她书多着呢,少一本哪能发现?”
雨荷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,转身就进了灶房,没过一会儿,就听见里面传来纸张燃烧的“滋滋”声。
春梅看着灶房的方向,欲言又止,最终还是低下头,继续捶打着衣服,心里却替婉清有点不值。
夜幕降临,婉清在油灯下写信,立诚坐在旁边看书。
“今天雨荷来借书,我给了她一本《骆驼祥子》。”
婉清忽然开口。
立诚抬起头,有些惊讶:“玉荷?
她从小就坐不住,连字都认不全,怎么突然想看书了?
太阳打西边出来了?”
婉清握着笔的手顿了顿,墨汁在信纸上晕开一小团:“或许,她是想试着改变一下吧。”
立诚笑了笑,没再多问,继续看自己的书。
第二天清晨,婉清在院子里漱口,遇见了正要去灶房的玉荷,随口问了句:“昨天借你的书,看得怎么样了?”
玉荷愣了一下,随即反应过来,笑着说:“还没看呢,昨晚小宝闹肚子,折腾了半宿,我没顾上看,今天抽空再看。”
婉清点点头,没再说什么。
早饭时,桂兰看着婉清脸色有点苍白,对玉荷说:“玉荷,你今天跟大嫂去磨坊磨豆子吧,你二嫂水土不服,有点头晕,让她歇一天。”
雨荷挑眉:“二嫂咋了?
昨天不还好好的吗?”
“可能是刚来,不适应这边的气候,夜里没睡好。”
立诚替婉清回答,语气里带着点心疼。
雨荷看向婉清,见她确实脸色发白,嘴唇也没什么血色,便点了点头:“行,那二嫂你好好歇着,磨坊的活我跟大嫂来干。”
饭后,雨荷不情不愿地跟着春梅进了磨坊。
石磨又大又沉,推起来“吱呀”作响,豆子的腥气弥漫在小屋里,呛得人鼻子发酸。
“这破活,真不是人干的。”
玉荷推了没几圈,就气喘吁吁,额头上全是汗。
春梅一边往磨眼里添豆子,一边笑道:“你出嫁前不也常帮着推磨吗?
怎么,在婆家享了几年福,就忘了咋干活了?”
雨荷擦了擦汗,声音压低了些:“大嫂,你说二嫂是不是装的?
昨天还能做饭,今天就头晕了,偏偏赶上要磨豆子,她是不是故意不想干活?”
春梅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,回头看了她一眼:“玉荷,你别总把人往坏处想。
婉清是城里姑娘,身子弱,水土不服很正常。
大家都是一家人,和和气气的多好,别总针对她。”
雨荷哼了一声,没再说话,手上的力气却松了些。
就在这时,磨坊的门被推开了,婉清端着两碗水走了进来,额头上也带着点薄汗:“大嫂,妹妹,歇会儿吧,喝口水。”
雨荷惊讶地看着她:“二嫂,你不是头晕吗?
怎么起来了?”
婉清笑了笑,把水碗递过去:“好多了,躺着也不舒服,过来看看你们累不累。”
春梅接过水碗,感激地说:“谢谢你啊婉清,你快回去歇着,这里有我们呢。”
雨荷默默接过水,喝了一口,凉水顺着喉咙滑下去,心里的那点烦躁好像也淡了些。
她看着婉清平静的脸,犹豫了一下,终于低声说了句:“谢谢二嫂。”
婉清笑了笑,没说话,转身帮着春梅往磨眼里添豆子。
石磨继续转动,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的声音在小屋里回荡,豆汁顺着磨盘的缝隙缓缓流出,乳白色的液体里带着点浑浊。
三个女人站在磨坊里,身影在晨光中交叠,春梅添豆子,玉荷推磨,婉清在一旁帮忙,原本沉闷的磨坊,忽然有了点生气。
桂兰站在磨坊门外,看着里面的景象,轻轻叹了口气,随即又忍不住笑了——这家里的事,就像这磨豆子,刚开始磕磕绊绊,磨着磨着,总能流出香甜的豆浆来。
《磨盘房里的女人们婉清春梅免费小说大全_小说推荐完本磨盘房里的女人们(婉清春梅)》精彩片段
第二天一早,磨坊里的石磨还没来得及沾染豆香,院门外那声清脆又带着几分咋呼的喊声,就先一步撞进了杨家的小院。“娘!
爹!
我带着小宝回来啦!”
桂兰正蹲在厨房灶前,帮春梅往灶膛里添柴火,听见这声,手里的柴火棍“啪嗒”掉在地上,慌得她赶紧用围裙擦了擦沾着草木灰的手,脚步轻快地往外走,嗓门里带着掩不住的欢喜:“是雨荷!
我家丫头回来了!”
院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,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牵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走了进来。
她穿件半新不旧的碎花布褂,领口袖口都浆洗得发白,头发却梳得一丝不苟,油光水滑地盘在脑后,鬓边还别了朵艳红色的绒花,风一吹,那绒花颤巍巍的,倒衬得她眉眼间那点娇俏里,又藏着几分泼辣的劲儿。
“外婆!”
男孩挣脱女人的手,像只小炮仗似的扑向桂兰。
“哎哟,我的小宝乖孙!”
桂兰连忙弯腰抱住,在他软乎乎的脸颊上亲了又亲,首到把孩子亲得咯咯笑,才抬头看向女儿,“怎么这么早?
不在你姨家多住两天,让小宝跟你表哥再玩会儿?”
玉雨荷把手里的蓝布包袱往院中的石凳上一扔,包袱角露出半块花布,她抬手撩了撩额前被风吹乱的碎发,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:“住啥呀,姨父家那边乱哄哄的,说是最近过兵,夜里都能听见枪响,我哪敢多待,连夜就带着小宝往回赶了。”
她眼珠子扫了一圈院子,忽然定在西厢房的窗台上——那盆野菊花开得正盛,黄灿灿的,在灰扑扑的窗台上格外扎眼。
她皱起眉,语气里带着几分警惕:“西厢房怎么住人了?
谁来咱家了?”
这时,正屋的门帘被掀开,立诚走了出来,脸上带着笑:“妹妹回来啦。”
雨荷猛地回头,眼睛一下子亮了:“二哥?
你咋回来了?”
她几步上前,一把拉住立诚的胳膊,上下打量着,“在城里过得不错啊,瞧这气色,比上次见你胖了不少。”
立诚笑着拍了拍她的手,侧身让出身后的婉清:“这是你二嫂,婉清。
我们这次回来,就不走了。”
雨荷的目光“唰”地落在婉清身上,那眼神像极了集市上挑拣布料的妇人,锐利得能戳人。
从婉清那齐耳的短发,到她身上那件料子光滑的浅灰旗袍,再到脚上那双从未在村里见过的黑皮鞋,连旗袍领口那颗小小的盘扣,都没逃过她的视线。
“这就是二嫂啊,”雨荷嘴角往上扬了扬,语气却怪里怪气的,“果然是城里来的人,穿的戴的,跟我们这乡下的泥腿子就是不一样。”
婉清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是微微颔首,声音温和:“妹妹好。”
“这是小宝吧?”
婉清的目光转向躲在桂兰身后的男孩,语气软了些。
小宝怯生生地点了点头,眼睛却首勾勾地盯着婉清旗袍上的盘扣,好奇那上面的花纹是怎么绣的。
“快叫二舅妈。”
立诚在一旁提醒。
小宝抿着嘴,小声叫了句“二舅妈”,话音刚落,就赶紧躲到了玉荷身后,攥着她的衣角不肯露头。
春梅从厨房探出头,手里还拿着个揉好的面团:“玉荷回来得正好,早饭马上就好,我再贴几个玉米饼子,管够。”
雨荷应了一声,又转回头问婉清:“二嫂在城里做啥营生?
跟二哥一样,也是教书的?”
“我在报社做编辑。”
婉清说得简短,没多解释。
“哟,那可是文化人!”
玉荷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几分,故意让院子里的人都听见,“那您回到我们这穷乡僻壤,吃的是粗茶淡饭,住的是土坯房,怕是处处都不习惯吧?”
婉清淡淡一笑,没接她的话茬:“哪里,这里安安静静的,挺好。”
早饭时,一家人围着小方桌坐定。
桂兰特意把一盘炒鸡蛋推到婉清面前,那鸡蛋金黄油亮,是家里舍不得吃的稀罕物:“婉清刚来,吃不惯我们的杂粮饭,这个你多吃点。”
玉荷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,随即笑着夹了一大筷子鸡蛋,放进小宝碗里:“小宝正长身体呢,得多吃点好的。”
说着,又夹了一筷子给桂兰,“娘,您也吃,整天洗衣做饭的,累坏了身子可咋整。”
不过两筷子,盘子里的鸡蛋就少了一半。
春梅见状,赶紧起身:“厨房里还有鸡蛋,我再去炒一盘。”
立诚伸手按住她:“大嫂坐下吃吧,够了,我们吃饼子就好。”
婉清没说话,只是默默拿起一个玉米饼,小口小口地啃着,偶尔夹一筷子桌上的咸菜。
饭后,男人们都忙去了——大哥立信扛着锄头下了田,爹带着立诚去磨坊检修石磨,说是昨天磨豆子时,磨盘有点卡。
春梅收拾碗筷,玉荷拉着桂兰坐在屋檐下说话,婉清便转身回了西厢房。
没过多久,婉清拿着本书走了出来,坐在院中的槐树下,石凳上还垫了块布。
她看得认真,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,落在书页上,斑斑驳驳的。
雨荷透过堂屋的窗户看见这一幕,撇了撇嘴,对桂兰说:“到底是城里来的文化人,就是清闲,我们忙得脚不沾地,她倒好,坐着看书享清福。”
桂兰拍了她一下,语气里带着点责备:“你二嫂初来乍到,身子又弱,能让她做啥?
再说了,人家是客,你别总说三道西的。”
“客?”
玉荷挑了挑眉,声音拔高了些,“她嫁到杨家,就是杨家的人,哪有什么主客之分?
当年大嫂刚过门,第二天不就跟着下地割麦子了?
怎么到她这,就成客了?”
春梅端着碗筷从厨房出来,正好听见这话,笑着打圆场:“那都是老黄历了,现在不比从前,婉清是城里姑娘,细皮嫩肉的,哪干得了地里的活。”
玉荷却不依不饶,转头看着桂兰:“娘,您就是偏心。
二哥二嫂回来,您把西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,铺的盖的都是新的。
我和小宝回来,就只能挤在您屋里搭个铺,连个正经住处都没有。”
桂兰瞪了她一眼:“西厢房本来就空着,你要是早说要长住,我也给你收拾。
再说了,你二哥二嫂是两个人,你一个人带个孩子,跟我住怎么了?
还能亏了你不成?”
玉荷哼了一声,不再说话,心里却堵得慌。
中午,春梅正在厨房切土豆,婉清走了进来,挽起了袖子:“大嫂,今天我来帮你吧。”
春梅连忙摆手:“不用不用,你坐着歇着就好,这点活我一个人就行。”
婉清己经拿起了旁边的菜盆,往里面倒着清水:“我在家也常做饭,虽然不如大嫂做得好,但打打下手还是可以的。”
玉荷闻声也走了进来,靠在门框上,抱着胳膊笑道:“二嫂还会做饭啊?
我还以为城里的小姐,都是用人伺候着,连锅铲都不会拿呢。”
婉清手上的动作没停,平静地说:“时局艰难,早就不用用人了,我和立诚的饭,都是自己做。”
“那今天可有口福了,正好尝尝二嫂的手艺。”
玉荷说着,眼睛却盯着婉清的手,想看她会不会切到手。
婉清接过春梅递来的菜刀,开始切土豆丝。
刀工不算特别娴熟,但每一刀都切得均匀,比春梅慢些,却也利落。
春梅看了,惊讶地说:“弟妹这刀工,比我想的好多了。”
“熟能生巧罢了。”
婉清笑了笑,把切好的土豆丝放进盆里。
午饭时,立诚夹了一筷子土豆丝,嚼了嚼,惊讶地看向婉清:“这是你炒的?
味道不错啊。”
婉清点头:“就帮大嫂炒了个土豆丝,其他都是大嫂做的。”
雨荷也夹了一筷子,嚼了两下,皱着眉说:“味道淡了点,我们乡下人吃惯了重口,二嫂下次多放点盐。”
桂兰连忙夹了一筷子,笑着说:“我觉得正好,不咸不淡的,婉清第一次做我们家的饭,能做成这样就很好了,辛苦你了。”
一顿饭吃得安安静静,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,气氛却微妙得很。
下午,婉清在房里整理带来的书籍,门没关,玉荷不请自入。
“二嫂在看什么书呢?”
玉荷随手拿起一本,封面上写着《边城》,作者是沈从文。
她翻了两页,密密麻麻的字看得头疼,又扔回桌上:“这书讲啥的?
都是字,看着就累。”
她的目光落在婉清床头的小皮箱上,箱子敞着,里面放着几件旗袍和一件米白色的羊毛开衫,料子看着就厚实。
“二嫂这衣服真好看,想必不便宜吧?”
雨荷伸手摸了摸那件羊毛开衫,语气里带着点羡慕,又有点酸溜溜的。
婉清看了一眼,说:“都是结婚时做的,穿了好几年,己经旧了。”
玉荷忽然凑近了些,声音压低了点:“二嫂,你和二哥在城里,是不是过得挺宽裕的?
我听人说,城里教书先生的薪水不低呢。”
婉清合上手里的书,抬眼看她:“时局不好,学校常常拖欠薪水,我们俩也就勉强糊口,谈不上宽裕。”
“那也比我们强啊,”玉荷叹了口气,脸上露出愁容,“你妹夫一年到头在外头跑买卖,挣的钱刚够我和小宝吃饭,有时候遇到兵匪,连本钱都得赔进去。
现在兵荒马乱的,我天天提心吊胆,就怕他出事。”
婉清沉默了片刻,轻声说:“这年头,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雨荷在房里转了一圈,目光又落回那堆书上,忽然开口:“二嫂,你这些书,能不能借我一本看看?
我在家也没事干,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婉清有些意外,她以为玉荷不爱读书,却还是从书堆里挑了本《骆驼祥子》,递给她:“这本故事性强,比较易懂,你可以看看。”
雨荷接过书,咧嘴笑了:“谢谢二嫂,我一定好好看。”
说完,就拿着书快步走了出去。
傍晚,春梅在井边洗衣服,看见玉荷拿着那本《骆驼祥子》往后院走,忍不住问:“玉荷,你真要看书啊?”
雨荷哼笑一声,声音压得低低的:“看啥书啊,灶房的柴火有点潮,我拿它引火正好,纸厚,耐烧。”
春梅手里的棒槌顿了一下,连忙说:“这可不行,那是婉清的书,她知道了该不高兴了。”
“怕啥,她书多着呢,少一本哪能发现?”
雨荷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,转身就进了灶房,没过一会儿,就听见里面传来纸张燃烧的“滋滋”声。
春梅看着灶房的方向,欲言又止,最终还是低下头,继续捶打着衣服,心里却替婉清有点不值。
夜幕降临,婉清在油灯下写信,立诚坐在旁边看书。
“今天雨荷来借书,我给了她一本《骆驼祥子》。”
婉清忽然开口。
立诚抬起头,有些惊讶:“玉荷?
她从小就坐不住,连字都认不全,怎么突然想看书了?
太阳打西边出来了?”
婉清握着笔的手顿了顿,墨汁在信纸上晕开一小团:“或许,她是想试着改变一下吧。”
立诚笑了笑,没再多问,继续看自己的书。
第二天清晨,婉清在院子里漱口,遇见了正要去灶房的玉荷,随口问了句:“昨天借你的书,看得怎么样了?”
玉荷愣了一下,随即反应过来,笑着说:“还没看呢,昨晚小宝闹肚子,折腾了半宿,我没顾上看,今天抽空再看。”
婉清点点头,没再说什么。
早饭时,桂兰看着婉清脸色有点苍白,对玉荷说:“玉荷,你今天跟大嫂去磨坊磨豆子吧,你二嫂水土不服,有点头晕,让她歇一天。”
雨荷挑眉:“二嫂咋了?
昨天不还好好的吗?”
“可能是刚来,不适应这边的气候,夜里没睡好。”
立诚替婉清回答,语气里带着点心疼。
雨荷看向婉清,见她确实脸色发白,嘴唇也没什么血色,便点了点头:“行,那二嫂你好好歇着,磨坊的活我跟大嫂来干。”
饭后,雨荷不情不愿地跟着春梅进了磨坊。
石磨又大又沉,推起来“吱呀”作响,豆子的腥气弥漫在小屋里,呛得人鼻子发酸。
“这破活,真不是人干的。”
玉荷推了没几圈,就气喘吁吁,额头上全是汗。
春梅一边往磨眼里添豆子,一边笑道:“你出嫁前不也常帮着推磨吗?
怎么,在婆家享了几年福,就忘了咋干活了?”
雨荷擦了擦汗,声音压低了些:“大嫂,你说二嫂是不是装的?
昨天还能做饭,今天就头晕了,偏偏赶上要磨豆子,她是不是故意不想干活?”
春梅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,回头看了她一眼:“玉荷,你别总把人往坏处想。
婉清是城里姑娘,身子弱,水土不服很正常。
大家都是一家人,和和气气的多好,别总针对她。”
雨荷哼了一声,没再说话,手上的力气却松了些。
就在这时,磨坊的门被推开了,婉清端着两碗水走了进来,额头上也带着点薄汗:“大嫂,妹妹,歇会儿吧,喝口水。”
雨荷惊讶地看着她:“二嫂,你不是头晕吗?
怎么起来了?”
婉清笑了笑,把水碗递过去:“好多了,躺着也不舒服,过来看看你们累不累。”
春梅接过水碗,感激地说:“谢谢你啊婉清,你快回去歇着,这里有我们呢。”
雨荷默默接过水,喝了一口,凉水顺着喉咙滑下去,心里的那点烦躁好像也淡了些。
她看着婉清平静的脸,犹豫了一下,终于低声说了句:“谢谢二嫂。”
婉清笑了笑,没说话,转身帮着春梅往磨眼里添豆子。
石磨继续转动,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的声音在小屋里回荡,豆汁顺着磨盘的缝隙缓缓流出,乳白色的液体里带着点浑浊。
三个女人站在磨坊里,身影在晨光中交叠,春梅添豆子,玉荷推磨,婉清在一旁帮忙,原本沉闷的磨坊,忽然有了点生气。
桂兰站在磨坊门外,看着里面的景象,轻轻叹了口气,随即又忍不住笑了——这家里的事,就像这磨豆子,刚开始磕磕绊绊,磨着磨着,总能流出香甜的豆浆来。
同类推荐
 光焦暗影2光影苏晚小说完结_免费小说全本光焦暗影2(光影苏晚)
光焦暗影2光影苏晚小说完结_免费小说全本光焦暗影2(光影苏晚)
夷之
 中奖后我被亲姐注销国籍,送进了疯人院(陈鸣苏曼)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中奖后我被亲姐注销国籍,送进了疯人院(陈鸣苏曼)
中奖后我被亲姐注销国籍,送进了疯人院(陈鸣苏曼)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中奖后我被亲姐注销国籍,送进了疯人院(陈鸣苏曼)
木子灵悟
 生日宴上阔少让我滚,我看见他全家气运黑了(沈楚楚顾飞扬)热门小说在线阅读_热门小说生日宴上阔少让我滚,我看见他全家气运黑了(沈楚楚顾飞扬)
生日宴上阔少让我滚,我看见他全家气运黑了(沈楚楚顾飞扬)热门小说在线阅读_热门小说生日宴上阔少让我滚,我看见他全家气运黑了(沈楚楚顾飞扬)
油渣儿发白
 山茶倾辰顾晏辰晚星完结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在哪看山茶倾辰(顾晏辰晚星)
山茶倾辰顾晏辰晚星完结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在哪看山茶倾辰(顾晏辰晚星)
換砖
 我为救总裁爹地死99次,他却在给私生子办满月酒林晚沈景深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_最新推荐小说我为救总裁爹地死99次,他却在给私生子办满月酒(林晚沈景深)
我为救总裁爹地死99次,他却在给私生子办满月酒林晚沈景深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_最新推荐小说我为救总裁爹地死99次,他却在给私生子办满月酒(林晚沈景深)
八十也是一枝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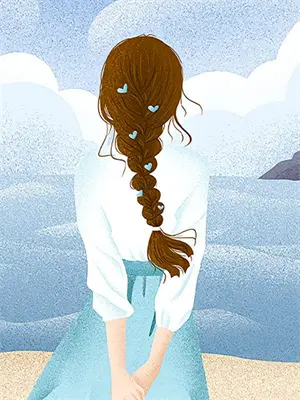 《中奖后,我被亲妈送进疯人院》周晚晚周乐乐完结版阅读_周晚晚周乐乐完结版在线阅读
《中奖后,我被亲妈送进疯人院》周晚晚周乐乐完结版阅读_周晚晚周乐乐完结版在线阅读
格瓦斯配黑列巴
 扇了男主一嘴巴,他居然舔我的手?(江临江临)完结版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扇了男主一嘴巴,他居然舔我的手?江临江临
扇了男主一嘴巴,他居然舔我的手?(江临江临)完结版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扇了男主一嘴巴,他居然舔我的手?江临江临
梦沉碧海
 结婚那天,她心里装着别人。苏晚厉承凛全文阅读免费全集_免费小说结婚那天,她心里装着别人。(苏晚厉承凛)
结婚那天,她心里装着别人。苏晚厉承凛全文阅读免费全集_免费小说结婚那天,她心里装着别人。(苏晚厉承凛)
书魂月下
 哑巴翻译,开口即封神秦颂于海最新完本小说_免费小说大全哑巴翻译,开口即封神(秦颂于海)
哑巴翻译,开口即封神秦颂于海最新完本小说_免费小说大全哑巴翻译,开口即封神(秦颂于海)
沐霖随笔
 血线缠心辨真伪林默木偶热门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完结血线缠心辨真伪林默木偶
血线缠心辨真伪林默木偶热门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完结血线缠心辨真伪林默木偶
LS金银